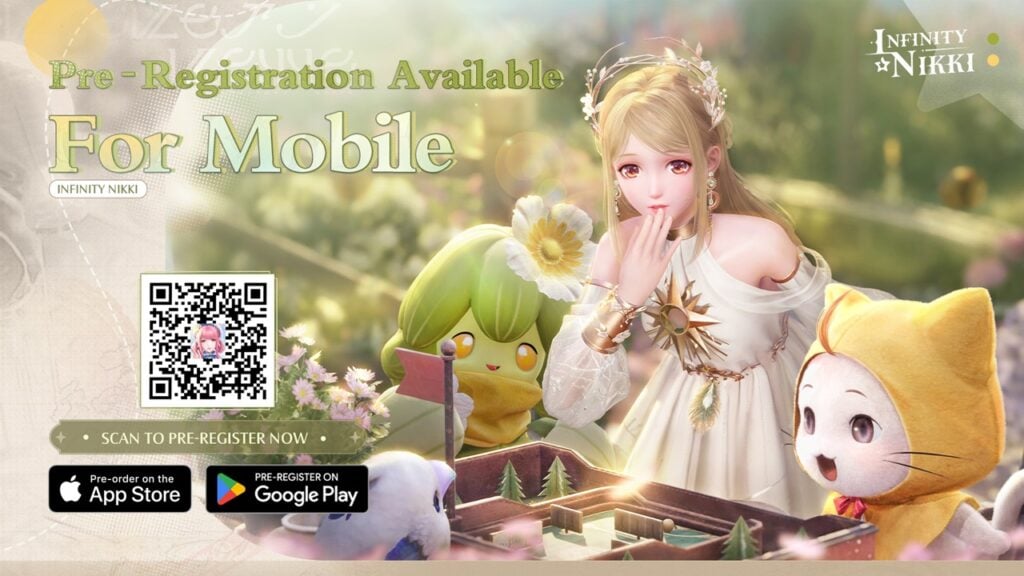羅德·瑟林《夜間畫廊》因風格獨特遭腰斬
- By Christopher
- Jan 06,2026
1945年2月,年輕的羅德·瑟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直面死亡,一名日本士兵在馬尼拉幾乎終結了他的生命。這個決定性的時刻——直視步槍槍口並接受死亡——永遠地塑造了這位未來的電視夢想家。正如《陰陽魔界》歷史學家馬克·齊克里指出的:「他絕對在想,『就是這樣了,我的生命到此為止了。』」
一位戰友的迅速行動救了瑟林的性命,卻未能拯救他的心靈。戰爭在這位作家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,這些傷疤影響了他貫穿整個電視黃金時代的開創性作品。儘管他後來以電視界的「憤怒青年」聞名,這些戰場經歷構成了瑟林深刻道德視野的基石。

黃金男孩
《獨行客》的首集〈號角回聲〉,向觀眾介紹了內戰老兵威廉·科爾頓上尉(洛伊·布里吉斯 飾)——一個在戰後美國社會中漂泊無依的人。瑟林的開場旁白捕捉了其精髓:「在被稱為內戰的血腥衝突過後,成千上萬無根、不安、尋找方向的人們向西遷徙……」
這種向西的漂泊映照了瑟林自己的戰後旅程,儘管他的道路最終導向好萊塢而非邊疆。到了1950年代,這位前傘兵已轉變為電視界最受讚譽的劇作家,憑藉《模式》和《重量級輓歌》等灼熱的劇作贏得了六座艾美獎和業內最高的稿酬。
「他是電視界的亞瑟·米勒,」齊克里評論道。
但圍繞種族暴力(特別是他受艾美特·提爾事件啟發而被擱置的劇本)等爭議性話題的審查戰,讓瑟林確信類型故事或許能提供更大的創作自由。他曾對女兒安說過一句名言:「外星人能說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不能說的話。」由此誕生了《陰陽魔界》——這個節目賦予瑟林前所未有的藝術控制權,讓他能透過推測性小說來探索人類處境。

獨行客登場
當科爾頓上尉在《獨行客》的試播集中維護一名落魄的邦聯老兵時,這一刻完美地體現了瑟林的人文主義世界觀。正如女兒茱蒂所言:「最重要的是,他有一種深刻的體面感。在他所做的每一個故事中,都試圖對人類的處境做出評論。」
這部系列劇讓瑟林得以繼續探索那些激發他《陰陽魔界》作品的主題——種族主義、正義、戰後創傷——而背景設定在美國西部。在一集強有力的早期劇集中,科爾頓因在戰爭最後一天殺死一名少年士兵而深受困擾——正是這種道德層面複雜的敘事,讓瑟林與眾不同。

然而,電視網高管期待的是傳統的西部動作片,而非對戰爭後果的哲學探索。正如齊克里解釋:「到了[那個時候],電視網想要的是不會為任何人辯護的節目。」當CBS以「暴力場面不足」為由在僅一季後取消了《獨行客》,這標誌著瑟林在電視界黃金時代的終結。
永不終結的戰爭
戰鬥造成的心理創傷對瑟林而言從未完全癒合。他的女兒安回憶起童年時發現父親因噩夢而心煩意亂的早晨:「他告訴我,他夢見敵人正朝他衝來。」這些戰場上的夢魘經常在他的寫作中浮現,尤其是在《陰陽魔界》的〈紫色預言〉這樣的劇集中,其中描繪了一名能預見戰友死亡的士兵。
在《獨行客》中,瑟林透過探討種族暴力的強有力劇本(〈萊繆爾·斯托夫的歸鄉〉)和戰後創傷(〈傷者之一〉)來宣洩這些經歷。後者包含了瑟林最令人心酸的一段對話之一:
費爾普斯:「我有時認為,一個人可能因殺戮而死亡,亦如被殺一樣。」
科爾頓:「這正是區別人與野獸的特性之一。」
儘管《獨行客》僅播出了26集,但它代表了瑟林職業生涯中至關重要的一章——這是一位從未對世間不公完全妥協的道德夢想家的作品。正如齊克里談及該劇最佳時刻時所言:「你會知道寫出那種東西的人是親身經歷過的。」

最新新聞
更多 >-

- 《泰莉絲托》結合骰子與牌組 數學驅動的 Roguelike 史詩冒險
- Jan 08,2026
-

- 手槍檯:癲狂肉鴿對抗無盡屍潮
- Jan 08,2026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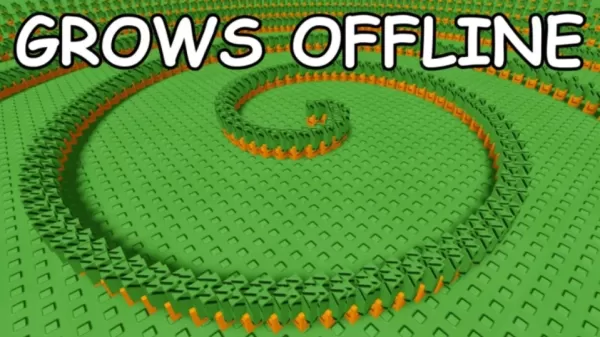
- 解鎖花園特殊種子培育指南
- Jan 07,2026
-

- 《Stumble Guys》超級英雄賽季:征戰暗影巢穴
- Jan 07,2026
-
- 百思買推出魔法風雲會補充包
- Jan 07,2026